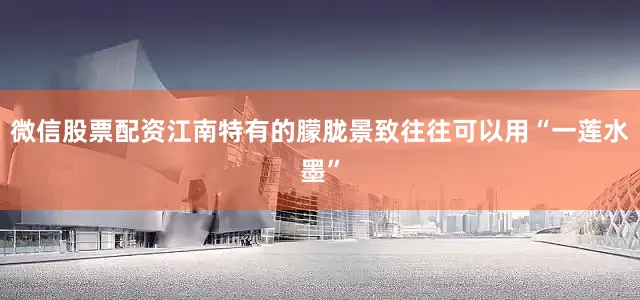
■ 张远平
一
梅雨时节不仅有荷花,而且独具韵味,花苞随意点缀其中,荷花沾着水珠轻舞,江南特有的朦胧景致往往可以用“一莲水墨”,写尽芳华。
“天赐宣平黄金土,地育宫廷白玉莲。”家乡武义宣平盛产莲子,因原产地得名“宣莲”。宣莲始植于唐朝显庆年间(656—661),清嘉庆六年(1801)被列为皇室贡品,历代文献誉其“冰肌玉质”。宣莲与湘莲、建莲并称为中国三大名莲,这一地位在历史文献、产地认证及产品价值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记载。
柳城,古称鲍村,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环城种柳树,数年后柳树成荫为城垣,从此鲍村遂称柳城。柳城,虽因柳得名,却因莲而兴。
据史料记载,宣莲最初作为观赏植物,从“一亩方塘”起步,被广泛种植于该区域的寺观和私人花园,此后逐渐演进为“眼观其华,口享其味”的农特产品,如今已发展出独特的“十里荷花长廊”,形成了“百种名莲竞娇姿”的视觉盛宴。
我也喜欢凑这份热闹,因为热闹的不仅是人潮。但我更喜欢老屋后面的半亩荷塘,独赏一池静荷,尤其是在雨中,听细雨轻叩荷叶,世界遂变小,只剩下一人一池荷。
展开剩余84%梅雨将歇的清晨,和着泥土翻新的味道,荷塘里氤氲浮起一层薄薄的青雾,荷叶丛中不知何时冒出了几根荷苞子,让多日的痴守一夜破防。晶莹剔透的水银珠子,在阔大的莲叶里上下翻转,不慎滑落却惊起几尾赤鲤出水,尾鳍拍水形成的波浪,让一排排荷叶上的露珠应声齐刷刷倾泻到水中央。
暮色渐起时分,老屋升起了袅袅炊烟,那是母亲开始做晚饭了。柴火香、饭米味、荷塘清香酿成独特烟火味,成为无数游子一生最熟悉不过的记忆。
最妙的是月亮爬上树梢时,蛙声忽然此起彼伏。片刻安静的间隙,你或许还可以听见鱼儿啃咬荷叶茎秆的声音,这该是一番怎样的《鱼乐图》。
莲子从青涩初成到花实相生的蜕变路上,总伴随一些让人经久难忘的情境。
在记忆深处,常与父亲一起荷塘垂钓。
六月末的荷塘,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父亲总是先帮我拣块平整的石头坐下,再将鱼钩准确地甩进荷叶间的空隙。在理想的状况下,用不了个把小时,就有七八尾小鲫鱼钓上了岸。也有时浮漂许久不动,倒有只蜻蜓飞停到竿梢上。我不禁纳闷,为何这蜻蜓不立在小荷上头,偏偏停在我的竿梢上。
父亲走了,荷塘也没了。十多年前村里要盖大礼堂,征用了荷塘。从此,家乡的莲与我渐行渐远。每年春节期间,都有外地的戏班子来到村礼堂唱戏。隐约中父亲静坐在前排,无言笑看生旦净末丑。父亲最爱看《珍珠塔》《何文秀》等剧目,对其中的“莲花落”情有独钟,忘情处时不时能哼上几句。
多少年后蓦然回首,生命中的荷塘,既不能少雨,也不能缺鱼。荷塘无鱼如同“梵婀玲上断了弦”,荷塘少雨则失去这份沙沙淅沥的自然乐章。荷塘的终极之美,在于天边小雨唤醒草木“挂着水珠的苍翠生机”,在于水下游鱼穿梭嬉戏搅动精神层面的沉睡。
二
《诗经》中对采莲场景的描绘,简练,灵动,至美。采莲不仅是劳动场景,更被赋予情感隐喻。如《国风·陈风·泽陂》中“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而现实中的采莲过程,更多的是艰辛劳作与收获。
我上学时的生活费用都来自父母的这份劳作与收获。
凌晨的荷塘,还浸在暮色里,父母早已踩着露水出发,有时得冒雨抢摘成熟莲蓬,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莲动下渔舟”的美好惬意。也许,他们急急地催促着全是“多卖几个钱,给芽儿买件新衣服”而已,但他们依然从中看到希望。
莲蓬采回来后需要破蓬取粒,至少经过三重工序,众多的环节我大多经历过。
首先是巧剥硬壳,将莲子平放在安装有小刀背的案板,沿刀背纵向轻推外壳至出现裂纹,再沿裂缝手工剥离,青玉般的莲子顿时滚落。我常因用力过猛,将刀痕刻在莲肉中,一抬头瞥见母亲的眼神里尽是心疼。
其次是褪去薄衣,先用指甲尖挑开莲子嘴部最厚处白膜,顺势轻轻旋转,使其自然剥离脱落。这感觉挺有意思,那份一气呵成的畅快感,正如陶艺大师滨田庄司所言:“最好的作品往往诞生于忘记追求完美的时刻。”
然后是莲心穿刺,用细铁丝对准莲子底部凸点垂直刺入,取出翠绿莲芯,但稍一偏斜就会捅烂整颗莲子。莲芯很苦,“生生无限意,只在苦心中”,古籍记载其苦寒特性被历代医家用于泻火除烦。
最后是炭火烘焙,需经初烘排湿、恒速脱水、高温定型等关键环节,其中翻动时机与干燥判定很重要,得有丰富的经验与技巧。
莲子最惧水湿,最绝的是雨天抢烘的情景,在整个闷热如蒸笼的烘房里面,父母硬是从无边风雨中亲手夺回了一年四季的生计账目。
如此三番五次下来,宣莲前后经过了12道工序,终于以独具醇厚的品质新鲜出炉:颗粒圆润饱满,表皮略微皱缩,色奶白或淡黄,肉厚芳香,质酥不糊,食而无渣。
《宣平县志》称“莲过七里垄,功价与参同”。意思是说,宣莲虽然品质极佳,但主产区范围仅限于“七里垄”内且难以扩展。
清代宣莲核心产区位于柳城、西联、泽村的狭小特定区域,其形成有赖于当地独特的“香灰泥”土壤和山泉灌溉。如今,一些地方曾尝试引进宣莲种植,均未获成功,或许间接证实了宣莲的不可移植性恰恰是其地理标志价值的终极认证。
宣莲品种稀有,营养丰富,与普通莲子具有明显的差异。烹饪也不一样,宣莲免浸泡,直接炖煮半小时即软糯,煮后酥而不烂、汤色清透。
莲子炖红枣是我们一家人多年来未曾改变的最爱。或晨间早餐,或午后休憩,或晚间睡前,吃上一小碗,整天都有一种神清气爽的能量。夏季添加绿豆、百合制作成冰糖宣莲汤,更是传统消暑秘方。
当然,最美味的还数莲子炖猪肚。这是一道兼具食疗价值与滋补功效的传统汤品,方法多样。最方便的一种是,将猪肚切条或块后直接放入冷水中,与莲子同炖,大火煮沸后转小火,避免沸腾过猛,再搭配辅料即可。
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学不可以已”,那时偏远山村的淳朴学生往往通过课本窥见山外的世界。而悄悄点燃我认知未来的文字火种,则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也洒在年少的我内心深处。
六七月时令,晚自修后的校园荷塘,仍有三三两两备战高考的同学,借着月光大声地吟背,恨不得“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一年,我有幸以高考文科应届全县最高分的成绩上了大学。
正如莫奈临终前对克莱门索所言:“我画的不只是池塘,是整个世界的呼吸。”在我的认知中,朱自清写的也不只是荷塘月色,而是整个世界的呼吸。
那些年,家乡的莲撑起了我对未来的憧憬;这些年,繁华褪去,便有了“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从容与恬淡。
莫奈晚年的《睡莲》系列(1914-1926)是其艺术生涯的终极蜕变,当白内障几乎夺走他的视力时,莫奈用那些颤抖的笔触,尽情描绘让观者听得见的光与水,任其在天地间交响。
有时痴痴地想,人生就是一朵莲,其绽放过程缓慢成长,需要耐心与沉淀,最终却快速归于纯粹与清净。
与《荷塘月色》的纯净美相比,老莲奉行“宁拙毋巧,宁丑勿媚”,以丑为美传达人物内在气质,有一种“水尽林空听天籁”的洒脱与率性。
被誉为“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的陈洪绶,自号“老莲”,幼名莲子。其笔下荷花常作奇崛之态,枯蓬挺若骨,勾莲瓣如铁,真乃融品格象征于笔墨。鲁迅曾评价“老莲的画,一代绝作”。
如果恰好来一场雨,留得枯荷听雨声,让雨也化成了墨,岂不更妙。《无常经》里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老莲残荷复成藕,又一个生命的轮回。宋代《宣和画谱》评徐熙残荷“寓兴于败芦寒苇”,暗示冬藏是为春生蓄力,死亡蕴藉新生。
年过半百,走过风雨,脑海里总会时不时跳跃浮现:荷塘,炊烟,父母,老莲,莫奈等等。
人生如莲,安守一隅,一晃也就老了。唯有莲子,生生不息。
发布于:北京市欣旺配资-线上配资-股市如何加杠杆-配资查询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